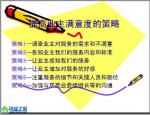哈耶克说过一句话:“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伏尔泰也说过一句话:“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我国物业管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业主自己的问题,然而当业主至今还没有认知到他的真实角色的时候,物业管理公司几乎同时扮演着“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双重身份,这是一种无法抗争也无从抗争的宿命。

有人说,城管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是中国改革以来一些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而我则认为,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恰好是物业管理。城管所面临的是权力的困惑,物业管理则正好相反,面临的是“民主”的困惑。近些年来,中国社区所发生的一些极具符号色彩的事件,譬如2001年深圳的邹家健先生景洲大厦维权、中海物管变局;2002年的深圳物管高层震荡、上海陆家嘴推出的服务论;2003年的《物业管理条例》;2004年的赵本山案、李文事件;2005年的北京朱明瑛案、郑州物管企业“罢收”、“深圳物业管理黑幕调查”,这种种的斗争,这一切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不可逆转的目标:社区的民主化。它最明显的标志是:物业企业从管理角色的跌落,已经导致业主权力的上升;社区威权政治的崩溃,推动了社区内广泛的政治参与,进而使社区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参与社会博弈成为了可能。
简单说来,物业管理无非是在两种模式作出选择:亲情化的开明专制和制度化的民主建设。在中国千百年来,社会是人际关系为本位的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它更重视“集体”和“家族”,早期的、中小城市的物业管理,仍然以一种亲情化的模式进行维系,然而在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在物业管理法规已经全面完善的今天,制度设计和民主变革方兴未艾的今天,现实却不断给予人冷冰冰的答案,原来,制度的改善,是要随一般的教育文化生活的提高,方能得到实际的效果,如果文化教育生活尚未达到某一阶段,而骤然绳以严峻的律法,就会发生以下的事态:
第一,公布的法律与隐蔽的事实,有完全处于相反的趋势,不合法的事实,并不能减少,这是物业管理的悖论。
第二,执法如果过严,一般无知的人民,容易对政府引起不满,无形中发生一种离心力,这是城管的悖论。
所以,在任何一个中国社区,都是三年而立(业主认识到自己为主),四年而不惑(物业公司再也哄骗不了咱们了!),五年知天命(知道究竟该交多少物业费),六年而耳顺(没有保修期,也和物管打不了多少仗了),七年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磨合期结束)。
作一种非常大胆的比较,今天的中国社区已经成为全世界政治历史的实验场,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历史突然被激活了,它发生了断裂、折叠、分岔和重组,各种各样的权力和组织,新的与旧的、成熟的与刚刚萌生的、刚性的与灵活的、法律的与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社会的与历史的,展开了搏斗、厮杀。昔日深圳的物业管理可以看作“新加坡式”民主政治的重演,深圳的物业管理早期即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威权政治”,对待违章我们毫不迟疑采取强制的、不限于停水停电的控制方法,业委会组织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而上海的物业管理则近似于韩国的政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就已经被韩国民众所拒绝了,连前任总统都一再被推向法庭,“参与”政策制定和立法的舆论勃兴,使上海市民已经体现出一种更高层面上的人文素质,从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可能;至于北京,由于华北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所以北京的物业管理更加近似于金融危机以后的印尼、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社区进入一种典型的“弱国家”形态,相形之下,全国范围的物业公司这几年的遭遇,都与世界各地的末代王朝譬如尼古拉二世、宣统皇帝颇为神似。
中国业主们针对开发商、物业公司和自身的一切斗争,其目的可以归结于一点:打造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至少在社区内部享受到充分“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是对以往计划经济思维下相辅相生的集中化、集权化、集体化的反动,而在这一诉求当中,包含着一切新生事物的希望。
(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06年第10期总第52期)
公地APP已正式上线!可在线阅读《现代物业》最新杂志,同时使用在线知识社区、参与沙龙研讨、自助知识学习……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及腾讯应用宝均可下载体验。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下载公地APP。】

或点击以下链接进行下载:http://dwz.cn/662k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