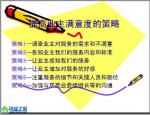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现代社区已具有了新的意蕴,那么对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而言,又需要什么机制来促成有效参与呢?下面我们就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通过对社区参与者的分析来理解现代社区参与的困境,继而寻求有针对性的对策。
第一,社区行为人就是普通的理性人,有着一般人类的趋利避害特性。很难想象一个在市场交易中精明算计的人会在社区参与中失去其经济人理性的本色,毕竟“关心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天性”[1],或者说自利假设乃是“所有政治学家惟一赞同的东西”[2]。比如,丘吉尔在国会演讲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座的每个人都有私人利益……我们不是一些没有任何私利、任何关系的人在这里集会,若是那样,就太可笑了。那可能在天堂会发生,但不是这个世界。” [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既然国家公仆在公共行政中都内含趋利性,那么在科斯意义上真实社区中,理性的社区人对实际社区事务的参与,同样也难以想象会绕开种种利益诉求而发生。这可以认为是社区参与的逻辑原点,即有利益才能激励参与;当然反过来也是对的,那就是如果风险或不利是显著的,那么社区参与也就不会积极了。
第二,我们的社区人多是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社区行动者不同程度地受到某些模糊的行事谚语之影响,诸如“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乃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尽管这些想法未必会得到正式认同,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规范作用却也不容武断否认。传统的行为逻辑揭示:除非必须,否则宁可无为。就社区一般的青壮年而言,他们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便是生计,为此要把大部分精力、时间、注意力和积极性投到市场与职场,偶尔有点闲暇,也是要么选择休息,要么选择在社交成本更低的虚拟空间里参与一下,找一点存在感和归属感。但对于物理的居住社区的参与热情,却也因此冷淡下来,甚至社区工作者自己也未必会对社区事务有太多热情。比如,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某社区,有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就曾坦率地告诉笔者,她几乎从未参与过自己所居住的另一个社区的事务,原因就是:觉得“没有参与的需要和必要”。此外,据笔者观察,一般社区工作者也不希望居民作为不速之客去找他们,比如,当笔者去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街道某社区居委会试图访谈社区治理事务时,就立即被工作人员警觉地回避掉了,同时表示“纪律所系,只能接受红头文件安排下的或上级打过招呼的调查访谈”。鉴于如此高的参与成本和比较低的参与效果,自下而上的参与实质上就是被“负面激励”了。

香港地区的社区参与活动
这样看,社区参与的匮乏也就不足为怪。前面提到的年轻人固然不必再赘述,就是社区中通常被认为参与度较高的老年人,其社区参与的惰性也显而易见。比如,大妈们的社区活动多集中在广场舞之类的健身娱乐项目,大爷们的社区生活却基本上不外乎是“宅”在家里、出来晒太阳、遛弯、下棋、打牌而已,若能有几个伙伴儿会心地聊天说笑,乃至能一起追求共同爱好,大概就算是相当高质量的社区社交了。所以说,社区参与的质量尽管是因人而异、因社区而异的,但对大部分社区成员来说,宁可选择不参与的倾向还是可观的。对此,有作者试图归因到历史惯性,认为“几千年积淀而成的私观念的国民心理特质……这些地区公共生活等级化而非水平型的组织方式,(使得)国民的概念被严重扭曲。(以至于)在居民个人的眼里,公共事务是别人(尤其是政府)的事务,而不是自己的事务。” [4]换句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理在社区中仍是惰于参与的挡箭牌,以至于“整个社区居民参与都有‘搭便车’的惰性和心态”[5],也许这也是激发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动因。简而言之,部分民众的慵懒、消极和不负责任的意识,客观上也在促使社区治理责任过多地集中到政府方面,进而促成社区行政化的泛滥。据笔者调查,相当多的社区居民(包括有知识的退休者)都在心底有一种“有事找政府”的情结,而对自己在社区中的义务和使命却不愿做认真的思考和承负。
所以套用哈姆雷特的句式来说,“参与还是不参与:这是一个问题”。人们一方面希望无为无害(这种惰性不妨叫做趋稳性),另一方面也在追求利益的满足(这种进取性不妨叫做趋利性)。于是,社区参与互动的实效,就取决于趋利和趋稳的行动者最终的选择,无论表现出积极还是消极,都取决于行动者在环境因素中的主观价值判断和追求。正因为此,所以“社区事务越和居民利益攸关,居民对其就会越关注,参与意愿也就越强” [1],换而言之,当人们觉得社区参与行为的价值(或收益)超过为之付出的代价(或成本)时,参与就可能发生,反之则反。当然,由于“个人效用函数要比新古典所假定的更复杂”[6],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社区居民也很可能没有完全相同的利益判断和选择。这样,尽管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寻求利益最大化,但这种偏好难免带有易错性(fallibility)[7]。也就是说,人们所认为有利的选择也许恰恰不能带来预期的效用;而真正能带来实利的行为,人们又偏偏觉得不值得做。典型例子就如“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等。
这种局限显然源于西蒙所谓的“有限理性”[8],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的理解总是建立在不完备的知识基础之上。”[9]在社区参与中,尽管普遍认为积极参与有利于共同体建设,但社区居民却未必都乐于这样做。其原因就在于,禀赋和认知各异的社区居民在具体的社区问题上,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认知和取舍。即便同样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算计,某些人倾向于参与,而另一些人则宁可选择不参与。也就是说,正因为人们对利益的理解是多元的、主观的,也是不完备的,所以人们对什么是要追求的利益目标总是存在差异化判断,反映在理论上就有了经济人理性、社会人理性以及刘太钢提出的所谓“传宗人理性”,或许还有不少信奉宗教的社区居民所怀有的那种“来世人理性”。就像德鲁克所断言的那样,宗教人士在社区生活中实践其信仰的运动,将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因为“他们的宗旨就是让社区活跃起来,鼓励大家采取行动,改善别人的生活”[10]。于是,人们就在这些多元的理性(也夹杂微妙的“情性”)中,形成不同的主观价值判断,而为了让人们有积极参与社区的事务,也就须从这些利益认知切入,并寻求内在的利益机制作为制度支撑。
第三,我们的社区人还是现代人。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无论人们对“乡愁”情结怎样怀旧,也无论对传统秩序如何眷恋,都不能不明确一个事实,即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作为历史趋势已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就像梁漱溟所理解的已被“破坏百年”的乡村那样[11],也在“创造性破坏”的洗礼中遭遇颠覆性变革。

城市化进程加快,更不利于社区参与的进行
德鲁克在《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中指出,铁路对工业化起到的是革命作用,它不仅创造了新经济区域,还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心智地理”(mental geography),而这种情况在高铁普及的今天将更为强化,导致人们的空间距离感越来越表现出相对性,让原先毗邻而居、相互守望的“小区域”生活共同体逐渐让位于更大范围的共同体。如果说铁路还只是拉近了“心智地理”,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彻底消灭了人们的距离感[10]。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买东西、读新闻、聊天、游戏等。东南西北、天涯海角的亲戚朋友及陌生人,都积极地涌入网络空间,在那里实现着另外一种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在发挥着活跃的市场功能,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正如毛寿龙教授所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坐下来相互了解的机会和时间都在减少,尤其是中国人又不擅长面对面的深谈,结果就影响了相互了解的质量,但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意外地发现社交成本在降低,而效率却得到提升。人们可以接触、认识更多的人,而朋友和熟人的概念也在被重新定义,比如微信的出现帮助人们开启了新的组合,不仅让传统的社会结构得到复兴(比如诸多的家族群、亲戚群、同学群等),还在促发新的社会结构。[12]
可见,未必只有老派的乡土秩序才算社区,也未必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能结成共同体,随着科技推动的社会变迁日益加速,共同体概念已不是原始秩序所能同日而语。早期人类的社交范围或许只限于家族、村落、乡里,但今天人们却拥有着更多的替代选择。不同地域,甚至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可在同一时间接受同一个新闻,思考并参与讨论同一个话题,甚至还可实现网民间的自发救助,事实上担负起传统社区的某些“邻里守望、相互扶助”的职能。比如诸多的网上捐助、预约献血等事件就在诠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同体内涵。所以说,与其为传统社区的衰落而哀伤,不如放开视野,沿循人们诉求偏好的转移轨迹,对社区的互联网元素予以充分尊重。马云说:“生活服务类电商好比是早上五六点的太阳。”[13]事实也果真如此,比如北京市曾打造社区一刻钟服务圈,其中包括市场购物的就近原则,但今天网购的方便事实上已经消解了这种服务安排的价值。人们在网上购书、买菜的模式在不少地方已成为常态。此外还有众多的社区服务的电商,诸如“云家政”、“小区管家”、“阿姨帮”等,都在见证新时代里社区共同体与市场共同体的有机融合,为现代社区共同体注入新的元素[14]。
白居易有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同样,就在人们怀疑社会资本被消解、在为“自己打保龄”而忧虑时,殊不知人们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热情却悄然有了别的选择和寄托。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他们之所以逐渐淡出某种社区活动,只是因为他们对那种活动已不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们已为自己的社交和归属感需求找到了成本更低、效果却也许更具吸引力的供给渠道,他们正在新的空间寻觅共同体的感觉,这是新技术为社区参与带来的重大变化。当年,滕尼斯之所以要刻意地将“共同体”与“社会”做区别,就是感受到了当时工业化的强劲冲击,同样,今天的信息化无疑也在对我们的社区概念进行颠覆性的重塑。
总之,社区之所以被称为共同体,就在于其成员依靠较强的共同体意识而凝合在一起,并能对本社区事务予以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15]。然而,旧有的共同体理念已在显著的行政化、个人行为的“惰性化”、及科技现代化冲击下有所变异。作为一种衍生现象,人们对所居住社区的活动缺乏了参与的热情(即便有参加者,也多是些退休老年人,或者寒暑假听学校老师安排来社区完成作业的中小学生);相比之下,作为社区主力的“青壮年”却在行政化的社区中近乎隐身,但这绝不代表他们的社会参与需求冷淡,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另一种空间,可以更好地容纳和照顾其各个需求层次。于是,他们就将宝贵的注意力资源投在了他们所认同的平台和形式。无疑,这将给“线下”的行政化色彩的社区建设形成新的挑战或竞争。假如社区建设中不能提供现代人所喜闻乐见的活动,那就很难吸引他们走出自身的“惰性”,或者放弃他们更感兴趣的“脱域社区”[16],而去参与他们不感兴趣的活动。当然,假如将社区活动也搬到线上,或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如前所述,这种趋势也在逐渐变成现实,人们期待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社区氛围的复兴和社会资本的回归。
综上所述,目前社区共同体的建设至少面临三种挑战:其一,行政化过浓的传统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效能;其二,社区居民自身带有的趋稳性、趋利性及主观价值论的有限理性(或易错性),都在社区参与冷漠症中扮演某种角色,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区共同体的分裂;其三,居民的行为选择固然有内在规律,而在新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这种行为机理会让居民选择更为经济便捷的社交参与方式,于是耗时低效、意义含糊的传统社区活动在逐渐失去吸引力,相比之下网上社区的互动却显露出方兴未艾之势。
随着参与的式微,传统社区的确有“不成其为共同体”的倾向。为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质量,并不能仅靠行政命令或各种宣传。事实上,限定内容和程度的动员型参与被认为只会“阻塞居民的参与意愿”[17];当然也不能仅靠一些形式化活动,而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让人们明确社区活动跟自身利益的关系及其界限,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内在的参与热情。同时要特别注意能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社区在“社会能做好的交给社会”的政策环境下,发挥充分的职能潜力,进而开创“多元共治”的局面,并在客观上协助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转变。当然随着社区参与效能的提高,民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得到真正弘扬。
总之,时代已变迁,过度留恋既往的社区氛围未免有些“刻舟求剑”之嫌;着眼未来,还需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理解人类行为机理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探寻现代社区的“共同体”治理之道。
参考文献
[1]王小章、冯婷. 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对H市的一项问卷调查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04(7):99-105.
[2]T. J.Lowi. Legitimiz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disturbed diss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ivew, 1993(3): 261-264.
[3][美]艾伦·沃尔夫著,沈汉等译. 合法性的限度——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20.
[4]张宝锋.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J]. 河南社会科学,2005(7):22-25.
[5]刘小妹. 城市社区参与机制之省思[J]. 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6):145-148.
[6][美]诺斯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0.
[7][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 上海:三联书店,1999:59.
[8][美]赫伯特·西蒙著,杨砾、韩春立、徐立译.管理行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06.
[9][奥]米塞斯著, 聂薇等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93.
[10][美]彼得·德鲁克著, 蔡文燕译.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M]. 北京:机械出版社,2006:6,8,41,52.
[1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11.
[12]毛寿龙.微信的社会资本逻辑[EB/OL]. http://maoshoulong.baijia.baidu.com/article/17958.
[13]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2013年3月3日.
[14]何志荣.“独自打保龄球”与“一起跳广场舞”:中国社区的现状与社区O2O实践[J],广告大观2014(12): 43-44.
[15]孙柏英、游祥斌、彭磊. 社区民主参与:任重道远——北京市区居民参与社区决策情况的调查与评析[J]. 2001(2):74-79.
[16]王小章、王志强. 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J]. 学术论坛, 2003(6):40-43.
[17]于莉. 城郊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社区参与状况:基于 326 位城郊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2016(2):72-8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5BGL197(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
景朝亮(1976—),山西洪洞人,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博士。
林建衡(1978—),河北衡水人,天津科技大学经管讲师,硕士。
(本文原标题为《论社区共同体的居民参与机理》,发表时有较多内容删减。)
(本文共同作者:林建衡,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16年第6期/总第359期)